奖杯的钨丝再亮,
照不亮,药瓶上那圈暗红的齿痕。
他们数日历,像剥开
一瓣瓣橘子般虔诚——
比念你烫金头衔时
更轻,更小心。
别把西装的折痕
叠成归途的沟壑。
所谓出息,不过是锦缎上
又绣了朵牡丹;
而厨房,那缕慢腾腾的白汽,
才是他们贴着心窝
焐了半生的炭。
若命运只给平凡的台词,
就,关掉简历的投光灯吧——
旧沙发里剥开的橘子,
正用,月光的绢布
包裹他们佝偻的脊椎,
比所有铜版纸奖状
更懂得,弯曲的弧度。
也请你们松开
风筝线般绷紧的眺望,
在窗台种茉莉,
用毛线团钓起整个下午。
晚年的甜味剂
不该是,系在邮戳上的等待,
而是搪瓷缸里
自己捂热的每一口晨昏。
我们练习孝的新语法:
不用完成时,只要现在式
当风,带着油锅的滋滋响,
翻动茉莉与橘皮的清香——
这世界小得恰好,
让三个标点符号
在餐桌旁坐下:
"在。"
"这。"
"里。"
照不亮,药瓶上那圈暗红的齿痕。
他们数日历,像剥开
一瓣瓣橘子般虔诚——
比念你烫金头衔时
更轻,更小心。
别把西装的折痕
叠成归途的沟壑。
所谓出息,不过是锦缎上
又绣了朵牡丹;
而厨房,那缕慢腾腾的白汽,
才是他们贴着心窝
焐了半生的炭。
若命运只给平凡的台词,
就,关掉简历的投光灯吧——
旧沙发里剥开的橘子,
正用,月光的绢布
包裹他们佝偻的脊椎,
比所有铜版纸奖状
更懂得,弯曲的弧度。
也请你们松开
风筝线般绷紧的眺望,
在窗台种茉莉,
用毛线团钓起整个下午。
晚年的甜味剂
不该是,系在邮戳上的等待,
而是搪瓷缸里
自己捂热的每一口晨昏。
我们练习孝的新语法:
不用完成时,只要现在式
当风,带着油锅的滋滋响,
翻动茉莉与橘皮的清香——
这世界小得恰好,
让三个标点符号
在餐桌旁坐下:
"在。"
"这。"
"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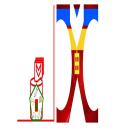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