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纳鞋底的声律
麻绳穿过布壳的刹那
哧啦——哧啦——
像极了某些话语
在唇齿间艰难穿行的轨迹
奖状薄如蝉翼
总在抵达她眼前时
突然失重
坠入灶膛明灭的火光
她手中的针尖
始终对准生活的裂缝
我们燃起的小小火苗
终年不见风
而老槐树的浓荫
是另一个叙事场
蚂蚁搬运着零星光斑
我把自己摊开在竹椅上
假装成一片
正在打盹的树叶
二、暗室
她的声音在此处
解开紧绷的缰绳
“老二陪旧台灯到半夜”
“老三记得王奶奶的水缸”
这些被放逐的褒奖
在闲谈的河流里
突然长出鳃
我的名字
第一次在别人耳中
泛起釉光
数学不及格的泪痕
被悄悄叠进补丁内里
此刻我忽然通晓
沉默如何炼成黄金
而某些倾听
需要保持假寐的姿势
三、苔学
袁枚的苔花在诗里开了三百年
我们趴在北墙根
用整个童年验证
背阴处的光合作用
母亲的言语是斜雨
从不正面浇灌
总借着夜露的名义
渗入石缝
她让我们相信
所有未说出口的
都在地下连成根须
米粒大的白花
也能让整面断墙
在四月保持缄默
四、家训的暗纹
颜氏在书页里咳嗽
曾文正公的家书
长满谦逊的苔藓
那些“暗修”“守默”的训诫
在族谱上盘成绳结
谢安捻须时
看见言语的背面
“常自教之”四个字
在魏晋的风流里
站成青石
我们家族的女性
早将这种哲学
缝进每道衣服的褶皱
当城市在朋友圈展览亲密
老屋依旧用暗语
守护种子的尊严
五、转译
如今她的白发
像深冬的芦苇
依然在家族聚会上
实施着语言的迁徙
当着姐姐的面
将我的加班翻译成勤勉
在弟弟身旁
把他的房贷重构为担当
这套密码已浸入骨髓
如黄河改道后
在地底继续奔涌
我们相继成为
新的河床
六、萌
滑梯的弧度
与老槐树的枝干惊人相似
小侄女眼睛里的星光
是我三十年前
存在母亲那里的
零钱
我蹲成新的树荫
对着空气发表宣言
“你看我们家萌萌...”
那个“萌”字
突然长出细根
扎进春天的皮下
她挺起的小胸膛里
有苔花在练习发声
而“哧啦——哧啦——”
正穿越两个时代的晨昏
在我喉间
生成新的年轮
七、暗香的力学
这不是遗传
是更精密的装置
像竹子在地底
用十年谋划一次破土
像梅花将香气
折成无数个弯
我们家族的女性
掌握着暗香的力学
当整个世界
都在练习高声部的赞美诗
我们依然用最低的音量
养护那些
尚未坚硬的脊梁
此刻我写下这些
忽然听见
无数个午后的纳鞋底声
正从笔尖涌出
它们不再需要
任何听众
麻绳穿过布壳的刹那
哧啦——哧啦——
像极了某些话语
在唇齿间艰难穿行的轨迹
奖状薄如蝉翼
总在抵达她眼前时
突然失重
坠入灶膛明灭的火光
她手中的针尖
始终对准生活的裂缝
我们燃起的小小火苗
终年不见风
而老槐树的浓荫
是另一个叙事场
蚂蚁搬运着零星光斑
我把自己摊开在竹椅上
假装成一片
正在打盹的树叶
二、暗室
她的声音在此处
解开紧绷的缰绳
“老二陪旧台灯到半夜”
“老三记得王奶奶的水缸”
这些被放逐的褒奖
在闲谈的河流里
突然长出鳃
我的名字
第一次在别人耳中
泛起釉光
数学不及格的泪痕
被悄悄叠进补丁内里
此刻我忽然通晓
沉默如何炼成黄金
而某些倾听
需要保持假寐的姿势
三、苔学
袁枚的苔花在诗里开了三百年
我们趴在北墙根
用整个童年验证
背阴处的光合作用
母亲的言语是斜雨
从不正面浇灌
总借着夜露的名义
渗入石缝
她让我们相信
所有未说出口的
都在地下连成根须
米粒大的白花
也能让整面断墙
在四月保持缄默
四、家训的暗纹
颜氏在书页里咳嗽
曾文正公的家书
长满谦逊的苔藓
那些“暗修”“守默”的训诫
在族谱上盘成绳结
谢安捻须时
看见言语的背面
“常自教之”四个字
在魏晋的风流里
站成青石
我们家族的女性
早将这种哲学
缝进每道衣服的褶皱
当城市在朋友圈展览亲密
老屋依旧用暗语
守护种子的尊严
五、转译
如今她的白发
像深冬的芦苇
依然在家族聚会上
实施着语言的迁徙
当着姐姐的面
将我的加班翻译成勤勉
在弟弟身旁
把他的房贷重构为担当
这套密码已浸入骨髓
如黄河改道后
在地底继续奔涌
我们相继成为
新的河床
六、萌
滑梯的弧度
与老槐树的枝干惊人相似
小侄女眼睛里的星光
是我三十年前
存在母亲那里的
零钱
我蹲成新的树荫
对着空气发表宣言
“你看我们家萌萌...”
那个“萌”字
突然长出细根
扎进春天的皮下
她挺起的小胸膛里
有苔花在练习发声
而“哧啦——哧啦——”
正穿越两个时代的晨昏
在我喉间
生成新的年轮
七、暗香的力学
这不是遗传
是更精密的装置
像竹子在地底
用十年谋划一次破土
像梅花将香气
折成无数个弯
我们家族的女性
掌握着暗香的力学
当整个世界
都在练习高声部的赞美诗
我们依然用最低的音量
养护那些
尚未坚硬的脊梁
此刻我写下这些
忽然听见
无数个午后的纳鞋底声
正从笔尖涌出
它们不再需要
任何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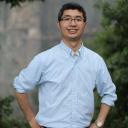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