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瓒
1968年生于江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诗集《松开》《哪吒的另一重生活》《周瓒诗选》,论著《透过诗歌写作的潜望镜》等。
李 琬
1991年生于湖北武汉,写作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出版诗集《他们改变我的名字》。曾获南方诗歌奖·青年诗人奖、第二届拾壹月诗歌奖·新锐诗人奖、第八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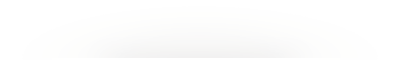
访 谈 人 :李 琬
被访谈人:周 瓒

“让身体先一步动起来”
李 琬:周瓒老师,您好!一直以来,我觉得您的诗让我感到亲切、共振。它既不是过度纤细、幽暗的,又并不经常使用高亢和强悍的嗓音,反而有许多幽默、间离的特征,而且在对现实进行勾勒和判断时也非常明快、直接、准确;它亲昵而又保持距离地凝视着身边的友人、亲人、爱人,乃至街头的陌生人,注视着来自他者的经验而非自我沉溺,善于在叙事中营造戏剧性……我记得您早年间在一篇文章里谈道:“只要耐心阅读一些优秀的,自80年代开始写作并持续写作的当代诗人的作品,或许人们就会看到一个个成熟中的诗人是如何伸展他们诗歌的触须,以达到在反复尝试的、对于日常经验的诗歌熔炼中扩大了的‘诗歌之胃’的。”(《诗歌写作中的“问题意识”》)近年来,您的写作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包含更多的公共性的主题和关切。我的理解或许并不准确与完整。可否请您自己简要描述一下,您的写作意识、风格乃至主题,在三十多年间有怎样的变化发展?
周 瓒:我的诗被你如此细致、准确地理解,让我意外又感动。有你这样的知音,或许我应该更自信也更积极一些。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对自己的写作进行一次总结反思。迄今我共出版了三本诗集:《松开》(2007)、《哪吒的另一重生活》(2017)和《周瓒诗选》(2019)。其中,《松开》记录了我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并获取一种坚定感的过程。我自大学时代开始写诗,那是1980年代中后期,但我比较晚熟。
《松开》中最早的诗作是1997年,那时周围有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在阅读和交流中,在“90年代诗歌”活跃的氛围之中,我的写作有了质的飞跃。我借着阅读、观影摸索属于自己的诗歌主题,在《影片精读》这组诗中完成了对自己声音的把握和自我的塑造。与其说我这组诗是一个青年学生运用知识编织自我并探寻意义,不如说跟我年轻时更腼腆内向,不喜直接谈论自己的性情有关。借助他人的故事,诗人说出了自己的紧张与怀疑、肯定和坚执。但是,这些表达中(尤其是观念的部分)的诗人依然显得莽撞和匆忙,意味着后来的我更多是处在修正与学习中。
后来,“他人的故事”裂变为“他人”与“故事”,我在剧场实践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同时也寻求诗歌风格与主题的变化。总体来看,是写作意识的一种打开,从语言表现到身体行动,意味着必须走出表达的旧方式,不指望等思想与观念完善了再说出来,而是先一步动起来,并观察这个过程,在过程中建立起新的感知方式和思维逻辑。体现在《哪吒的另一重生活》中,尤其是2008年左右开始的转变,确实如你所说,是我的诗歌声音的丰富化,在主题与关切上,我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与现实,也含纳了社会议题,因而有了某种公共性。
李 琬:在写作和批评之外,您也做了很多戏剧的工作,但是近年来这些活动似乎有所缩减。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未来还会继续这方面的尝试吗?
周 瓒:2007年至2019年左右,是我致力于戏剧工作的时期,后来这些活动一度缩减,与我的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变化有关,因我需要把更多时间与精力放在教学与科研上。不过这两年我又重启了这方面的尝试。今年五月,我完成了编剧和导演的帐篷剧《天空是一所大学》的试演,目前还有两个戏剧项目正在进行。
李 琬:非常期待您带来新的戏剧作品。除了诗人身份之外,您也是批评家和出色的学者。我们知道,您是洪子诚先生的弟子。他的分寸感,他对个体与时代之关系的把握,也都体现在您的研究和行文中。不仅如此,您也从事翻译,您在翻译阿特伍德和普拉斯等外国诗人作品方面贡献了大量的耐心和劳动,让我们读到了高品质的译文(《吃火》《爱丽尔集》),以及有关这些诗人的精彩的评论文章。学术研究和翻译对您的写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诗人、学者、译者、戏剧工作者等等好几种不同身份之间,有没有一种身份是“首要”的、您最重视的?
周 瓒:洪老师在学术工作中的分寸感与敏锐洞察力一直激励着我。在从事批评与翻译之初,我意识到理论研究与批评也是独具创造性的工作。我把学术研究与翻译看作对写作的激发,好让自己不要堕入各种偏见以及僵化的思维状态中。在各种身份中我选不出一个“首要”且是我“最重视的”,但诗歌与戏剧创作带给我的痛苦与愉悦,总使我对之保持盎然的兴致。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你,在你看来,写诗、写散文,也翻译诗与小说的你会更看重哪一种工作?
李 琬:散文像是生活自然的分泌,而写诗则是因为遭遇了一些更为尖锐、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四五年来,对待翻译工作,我自觉是认真用功的,不得不投入很多时间、精力。此外,目前我仍然需要参与一些其他的全职工作(比如作为编辑)来获得更为稳定、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收入。在我心目中,所有这些都有某种共通性和“向心”性,它们是有机一体的,都安放着我的某些精神活动,而不是彼此割裂的。正因为我能在不同性质的事情之间有所切换,我才维持了思考的弹性和余裕。如果一定要选择的话,我最看重的应该还是身为一个作者——无论文体是什么。不过我不是一个很有“规划”和野心的作者,我自己的所有写作,都几乎是在生活和工作的空隙、间歇中完成的,因为它需要外部生活的激发,它是对现实生活以及内心体验的某种反应:消化、总结、反抗、升华和重塑。
接下来我想略略离开我们自己的创作,说到一些有关诗歌总体现状的话题。近些年,我们都参与了不少高校诗歌奖、青年诗歌奖的评选工作。坦率地说,在我看来,其中平庸和糟糕的投稿,与其中写作成绩尤为突出的那些作者,在水准上有巨大的差别。前者有某些共同点,包括不注重结构和整体感,抒情往往囿于封闭的独语,缺乏对现实的判断与思考;而后者,即那些出众的作品,的确展现了一些吸引我的、新颖的、和过去二三十年诗歌不太一样的特质,比如说,那个非常个人化的“我”好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我们”这一抒情主体重新出现了,比如没那么倚重日常生活经验,不那么关注生活细节,而更多是从思想或情感或感觉本身出发(当然这种趋势走到极致也会有抽象化的风险)……您对目前青年的诗歌写作,乃至整个当代诗歌的发展趋势,有哪些观察和评价?
周 瓒:我同意你对青年诗歌写作的基本观察,如果有需要补充的,那就是有一个现象在我看来挺重要,即新一代青年诗人中女性诗歌的聚合力和原创性更强大。我注意到,你、苏晗、李娜、康宇辰、张慧君、张媛媛、陈陈相因、王井、梁京、曲晓楠等(这个名单你可以增添,我估计值得讨论的女诗人人数超过20位)新一代女性诗歌作者,已经自觉地将性别意识内在化为感受与观察的方式,并形成了清晰的、可辨识的风格与声音特征。她们以面貌各异的诗歌形塑了一个可与这个时代流俗抗衡的、整体性的“我们”(Women)。
李 琬: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近年来,尽管写诗的人不算少,但诗歌的读者和市场在萎缩。当然,有一些诗人成了畅销书作者和“网红”,获得了众多读者和粉丝,然而这种名声和销量并不意味着他/她的写作成就,可以说,与其写作成就、与其对语言和对诗歌的贡献不成正比……您如何看待这种现状,您会因此对诗歌感到失望和悲观吗?
周 瓒:作为当代文学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对那些压抑文学生长的力量更为敏感和不安,因为只要回顾一下20世纪文学史,我们便能发现,写作者一旦放弃了文学和美学立场的独立性,转而顺应潮流追逐个人的名与利,都肯定会使写作蒙上可疑的、虚假的、投机的阴影。因此,写作者的队伍庞大与否不是主要问题,成问题的是在这个写作群体中,那些看起来成功的诗人对语言、思想的贡献是否经得起时间与经典标准的考验。成为网红的能力与成为好诗人的能力也不一定相称,文学史上有太多昙花一现的例子。我倒是不悲观,因为悲观是老年人愤激于时代的方便托词。与其悲观,不如多一点警惕,以获得清醒和从容。
李 琬:作为学者,您不仅研究当代诗,更研究对于诗歌的批评和批评史。您认为目前的诗歌批评还有哪些不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
周 瓒:因前些年对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脉络做过梳理,结合自己工作的不足,我认为,当前的诗歌批评有两个方面亟待深入。一是尽快建设可靠的现代汉语诗歌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对于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新诗该怎样解读,形式因素有哪些,风格可能有哪些,目前还没有能获得大家认可的理论;二是需突破旧有的批评话语模式,现有的诗人论和诗歌批评不外乎几种模式,如以出生年代把诗人划归一个年代(从所谓的70后,到现在的90后、00后等),接着在关于这个年代的想象性的文化逻辑中求证诗人的表达,但又不去分析年代之间的关系。群体研究也经常会借用年代叙事,却总感觉是为了简便聚拢一群人而采取的方式。而谁能解决以上问题呢,我对近年发起和参与“未来诗学”讨论的中青年学者和诗人抱有期待。
批评当代诗歌批评于我是一种反思,而且这项工作意味着:我自己没有做好,是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好好做的。所以,我更想听你谈谈你对当代诗歌批评的期待。
李 琬:或许,我觉得从读者的角度,也可以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有限,只是为自己格外注意的几位诗人写过几篇文章。不过我的确有一些意见。粗略来说,问题有几个方面:首先,我个人觉得,当下的许多批评文章常常习惯于过快地从诗歌中提取片段的词句,并非从整体上对诗歌进行动力的、结构的、意识形态的分析,然而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仍然应该一方面从历史的,另一方面从文学价值的角度,给出对于诗歌质地的判断,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非仅仅中性化地、不痛不痒地去描述某些作品的特征、主题、写作手法;其次,在许多批评中,我还没有看到足够的历史感,似乎许多论者仅仅是针对诗人个体的写作静态化地去谈论,缺乏一些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下来理解诗歌的耐心;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大多数批评仍然围绕着一些已经获得众多读者、拥有“咖位”,甚至被经典化了的当代作者展开,还没有足够重视一些更为年轻但写作风格突出的作者(我还是很想举出郑越槟的例子)。
这就引发了我下一个问题。我自己作为女性作者,一方面,感谢和珍视我至今受到的许多真实读者和写作同行的认可、激励,但另一方面也时而感到困惑——这些困惑不只在女性作者身上存在,但又在我们身上特别突出——比如,在许多场合,我感到自己的作品无法得到充分的、严肃的讨论和审视,即使我认真读了对方的作品,自己的作品却也缺乏某种同等的阅读和反馈;在有关女性写作这一主题的会议上,往往很少有男性学者参与出席,即便出席,或许也并不真正关心这些话题……我想请您具体谈谈,在您看来,女性写作究竟面临着哪些困难和限制,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周 瓒:联系到你前面提到的有关诗歌批评的问题,我就在这里接着谈一下。一方面,对女性写作者个体缺少严肃、充分的讨论和审视,缺少与男性对等的阅读和反馈,这是文学批评与接受史上由来已久的情况;另一方面,当如今作为群体和现象的女性写作获得了集中的、专门的对待时,女性写作者又面临着被集体孤立的危险。这似乎是个无解的悖论处境,不过,身为女性,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在这种困境里开辟出路。我们可能需要在辩难与肯定中迈步,既要不断为女性写作正名,还要将性别议题与文学和现实的各种话题密切关联起来,同时,在言说策略上,要能够发明一种新的对话结构,在各种相交叉的话语中寻求诸如“既……又”“是的……但是”的交流氛围,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撕裂现场。在话语交锋中,这不是保守的退让,而是耐心的坚持。回到具体的批评工作中,即便是对女诗人个体的研究,我们也要有意识地把她的写作实绩放在女性写作传统和由男权话语主导的文学史脉络中兼顾对待,并且不惧于公正评价她(们)在文学史上较之于她(们)的男性同行更出色的部分。
李 琬:您说的对话结构非常重要,也让我共鸣。从性别的角度来阅读和批评诗歌,需要的不仅仅是非此即彼的理解,而是在既有的话语脉络中进行更为细腻的辨析。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您之前所说,女性写作已经呈现出非常丰富的面貌,而目前的批评似乎还没有充分呈现不同女性作者各自独特而强悍的声音,也许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在国内得到了大规模引进出版,媒体上也不乏相关讨论。与此同时,在和同龄女性朋友的交流中,我感到我们的确在生活中,在和男性相处方面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困惑,似乎两种性别并没有因为广泛的讨论而进一步相互理解,甚至反而更加难以相互理解,变得矛盾重重。我想,这是一个和写作无法完全割裂开来的现实生活问题。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问题,也和整个社会的“原子化”趋势有关,大家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烈了。在这样的环境下,女性作者面对的压力是多层次的: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情感上的;既来自男性主导的文化秩序,又来自自身内部……不知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在您看来,这些现象是否为女性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或提供了某些新的动力?
周 瓒:确实,如你所说,近年来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和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大规模的引进出版,且时不时在媒体上引发热议。正因如此,才在现实生活中激发出了你所体验到的两性矛盾和冲突感吧。大概在我们的期待中,男性读者也应该接触与接受了女性主义理论,或至少通过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多少理解并开始关注女性的困境。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顽固地遵循男性精英沿袭的宏伟命题,无暇领会甚至无视现实和历史中女性的感受。我们当然知道,不是所有男性都能达到共情另一性的境界,因为他们总是以人类之名谈问题,但人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两性共同构成的集体。对于男性而言,抽象地谈论人类(且这个人类总以男性为代表)是他们必须克服的问题,面对女性主义的冲击,这类男性如果一直待在原有的话语舒适区,那他们在思想上肯定是走不远的。以上是我对文学和批评现场中的男性同行的一点看法。
另一方面,作为当代诗歌和诗歌批评的观察者,我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大量译介到中国以来,性别研究作为批评视角并没有真正在诗歌批评与文学研究中得到贯彻。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这里的性别研究指的是不仅研究女性写作者,而且也用以讨论男诗人、男作家的理论视角;不仅研究经典的文学话题,也研究新的性别现象和各种性别亚文化表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是分裂的。此外,如果只是女性单方面的批评、抗争和反思男权话语显然不够,即便理论和作品译介过来了,如何接受,如何使更丰富多元的性别观念得到普遍的更新与拓展,依然显得急迫。当代女性不但需要女性意识的自我启蒙,还要争取和团结认同女性主义立场的男性(换言之,男性也需要性别启蒙);在厘清与性别有关的具体问题,在辩驳中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的同时,还需要有将这些问题加入当下的文化实践议题中的意识。
谈到现实生活中社会“原子化”之下个体的孤独感与压力,当然是一个总体的社会现象,而借助性别视角,依然可以触动和深入这些问题。前面说到,性别研究不是单一性别一方的申诉或抗辩,而是同时召唤男性加入的两性共同协作与进步。目前我们已经步入了这个阶段。用一个略显赶时髦的短语,我想说,无论何种性别,“以性别为方法”,或许可以将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同他人与社会相连接。这是值得尝试的。
李 琬:谢谢您精彩而深刻的回答。我想最后这个问题很难完全用语言去解释。正如诗歌本身一样,它要求着我们在平淡而艰难的生活中,不仅用思想而且更要用行动去“超克”自我,同时克服外界的难题。也许,改变我们周围的一点点小环境,和周围的不同性别的同伴都多一些面对面的而非抽象和线上的交流,似乎是让写作和生活展开的比较具体的方法之一。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
{Content}




















除每日好诗、每日精选、诗歌周刊等栏目推送作品根据特别约定外,本站会员主动发布和展示的“原创作品/文章”著作权归著作权人所有
如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用于他处和/或作为他用,著作权人及本站将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诗意春秋(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京ICP备16056634号-4 京ICP备16056634号-1 京ICP备16056634号-2 京ICP备2023032835号-2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4246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